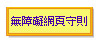第三章
公眾關注的法援案件
Ubamaka Edward Wilson 訴 保安局局長(FACV 15/2011)
尼日利亞國民Ubamaka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因販毒在香港機場被拘捕,經定罪後判處監禁24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保安局局長向其發出遞解離境令。Ubamaka先生在快將獲釋之際,於二〇〇六年九月七日向香港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要求給予難民身分,聲稱根據尼日利亞法例,他擔心會再被檢控而須面對一罪兩審。二〇〇七年三月,他另外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根據公約,被遞解離境者如被遣返原居國家後可能遭受該國官員施以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待遇,可抗拒被遞解離境)提出申請。他的難民身分申請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被拒。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Ubamaka先生因行為良好,在服刑16年後獲釋。在他獲釋後,政府隨即命令把他遞解離境,遣返尼日利亞。Ubamaka先生獲批法援,提出司法覆核,挑戰遞解離境令的有效性。
政府的論據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條例”)第11條使無權進入及停留於香港的人,如Ubamaka先生,不能援引《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憲制權利以挑戰遞解離境令。“人權條例”第11條訂明,“ 對於無權進入及停留於香港的人來說,本條例不影響管限這些人進入、逗留於及離開香港的出入境法例,亦不影響這些法例的適用”。政府憑藉“人權條例”第2(2)條規定“《人權法案》受第III部規限”。由於第11條屬第III部,故該條文凌駕於《人權法案》所賦予的權利,包括《人權法案》第11(6)條拒絕被遞解離境的權利,以及《人權法案》第3條針對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簡稱“不人道待遇”)的權利。另外,政府認為本案沒有任何構成不人道待遇情況的證據。
Ubamaka先生的論據是,如他被遞解出境至尼日利亞,即使他在香港已因販毒而入獄16年,仍可能因上述罪名而再次被檢控及判刑。執行遞解出境令將使他遭受《人權法案》第11(6)條所禁止的一罪兩審,以及該法案第3條所禁止的不人道待遇。此外,他辯稱“人權條例”第11條所施加的限制違憲,並必須以狹義解讀或與“人權條例”完全分割,使他不會因“人權條例”而不能援引《人權法案》第11(6)條及第3條。
原訟法庭裁定Ubamaka先生有可能面臨一罪兩審,因此把遞解出境令撤銷,但上訴法庭則裁定恢復執行該命令。Ubamaka先生繼而上訴至終審法院。
有關一罪兩審的理據,終審法院同意下級法院所言,在法律上,Ubamaka先生不能援引《人權法案》第11(6)條所提供的保障,反對執行遞解出境令,因為該保障已被“人權條例”第11條的條文豁除,而免受一罪兩審的權利並非不可減損及絕對。由於Ubamaka先生被界定為第11條所訂無權進入及停留於香港的人,終審法院裁定,根據《入境條例》第20(1)(a)條所作的遞解出境令,不會受“人權條例”的條文(包括《人權法案》第11(6)條)影響。終審法院總結時亦指出,“人權條例”第11條符合《基本法》第39條,在憲法上是有效的。
至於不人道待遇的問題,政府辯稱,對於Ubamaka先生聲稱返國後可能遭受不人道待遇,政府沒有義務去考慮這問題。終審法院駁回這論點。終審法院裁定,《人權法案》第3條有關保障免受不人道待遇的權利是絕對及不可減損的權利,“人權條例”第11條不能凌駕其上。不過,終審法院認為,本案的證據未能證明Ubamaka先生會遭受的對待,其嚴重程度會相當於《人權法案》所指的待遇或處罰,結果一致駁回Ubamaka先生的上訴。
終審法院的裁決釐清了“人權條例”第11條所載有關出入境法例的保留條文在憲法上的有效性、適用範圍及影響,以及該保留條文對《人權法案》的影響,因為《人權法案》禁止一罪兩審及施以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